Copyright © 中国民间人才网 京ICP备202301744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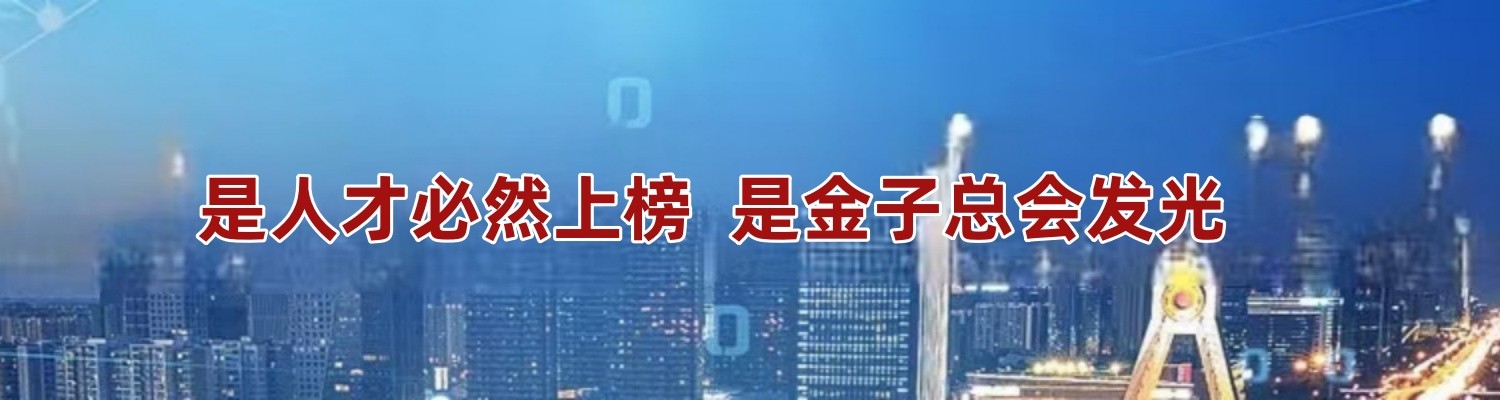

邓绍宽(四川)


引言:小说根据《三联生活周刊》人物新闻报道素材改编创作。以纪念我在山区与每月领七元补助的民办教师一起工作生活的特殊岁月。
1994年的夏,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成都平原上。火车站的喧嚣裹挟着热浪,知了的嘶鸣在油腻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尖利。十八岁的艳敏,像一株刚抽穗的麦苗,青涩而脆弱。她紧紧攥着那张汗湿的绿皮车票,指腹反复摩挲着“台江”两个字,仿佛那是通往母亲病榻的唯一符咒。薄薄的衬衫洗得领口起了毛边,贴在背上,洇开一小片汗渍。三十块工钱贴身藏着,沉甸甸的,是她刚在毛线厂用无数个日夜的疲惫换来的,能买药,能买肥,能解家里的燃眉之急。
“妹子,找活儿不?”声音像两块砂纸在摩擦。两个穿着不合时宜花衬衫的女人凑过来,廉价的雪花膏味混着汗味,熏得人头晕。胖的那个蒲扇摇得呼呼响,“电子厂,管吃管住,一月顶你干俩月!”
艳敏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脚边的蛇皮袋蹭着水泥柱,发出窸窣的声响。里面是她全部家当:两件旧衣,母亲熬夜烙的红薯干。“俺……俺得回家收麦子。”她声音细弱,眼睛慌乱地瞟着检票口上方的时刻表,心算着那趟归家的长途车还有多久启动。
“傻妮子!”瘦女人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力道大得像铁钳,“收麦子能挣几个钱?你娘要是知道你能挣大钱,病都能好一半!俺侄女上月刚寄回五百块呢,崭新的票子!”
五百块!艳敏的心猛地一跳。母亲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像破旧的风箱,一下下抽着她的心。那五块藏在鞋垫下准备买冰糖的钱,此刻像块烙铁烫着她的脚心。她看着两个女人“热切”的脸,那热切背后是深不见底的黑。嘴唇被咬出一道白印,她鬼使神差地点了头。
走出站口的瞬间,一股热风卷起地上的废纸,扑在她的脚面上。她弯腰去拂,一张绿色的纸片却从她敞开的衣兜里滑出,被风卷着,打着旋儿,轻盈地飘向远处纵横交错的铁轨,越飘越远,最终消失在刺目的阳光里。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归途。
她不知道,那阵风,也把她吹向了命运的深渊。
一天一夜的火车在山区一个小站停了五分钟,足够一行人走出车站。拖拉机的突突声在太行山的褶皱里爬行,像垂死的喘息。车斗里弥漫着羊粪、麦糠和汗液的混合气味,熏得人作呕。艳敏蜷缩在麻袋堆的角落,麦芒刺进脖颈,又痒又痛。暮色四合时,拖拉机停在一个被大山紧紧箍住的山坳里,黑黢黢的,像一口倒扣的铁锅。她被粗暴地推进一间低矮的土屋,门“哐当”一声关上,紧接着是铁链缠绕门闩的冰冷“哗啦”声,锁死了她的世界。
黑暗里,只有自己的心跳声在土墙上撞出空洞的回响。她摸索着墙角,指尖触到一袋坚硬的东西——老鼠药。三天水米未进,绝望像冰冷的蛇缠绕住心脏。她把那包苦涩攥在手心,像握着最后的选择权。
门开了,刺眼的光线涌入。一个穿着打满补丁蓝布褂的老汉佝偻着背,手里攥着一个红布包。他打开布包,一沓皱巴巴、沾满汗渍的纸币散发着陈旧的气味。“两千七,人我领走了。”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他身后站着一个壮实的黑脸汉子,眼神浑浊,带着浓重的酒气,直勾勾地盯着她,那眼神不像看人,倒像在牲口市上估量一头羊的斤两——那是刘三。
她被刘老汉拽着胳膊拖出屋子。山石嶙峋的小路硌得她光脚生疼。她回头望了一眼那间囚牢般的土屋,墙角那半袋老鼠药像一只沉默的眼睛。她松开了手,任那包苦涩的粉末无声地滑落在尘土里。被拐卖了。这个冰冷的事实,终于像淬毒的针,刺穿了最后的侥幸。
刘家的土坯房比关她的那间更破败。屋顶的茅草稀稀拉拉,山风一过,簌簌地往下掉灰土。炕席破旧,散发着陈年的汗酸和霉味。刘老汉把红布包往炕桌上一拍:“这是俺儿刘三,以后你就是他屋里人。”钱币的边角磨损得圆钝,像被无数双贪婪的手摩挲过。
“新婚”夜。一盏如豆的油灯在炕桌上摇曳,昏黄的光晕在斑驳的土墙上投下扭曲晃动的影子,像一张张无声嘲笑的鬼脸。艳敏把自己死死地蜷缩在冰冷的炕角,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肉体的刺痛抵御着灵魂的撕裂。刘三满身酒气,踉跄着扑过来,带着牲畜般的热烘烘的气息。
“给……你给两百,”他喷着酒气,舌头打着结,从脏污的裤兜里掏出两张同样皱巴巴的百元票子,在她眼前晃了晃,“你就能走。”
走,艳敏猛地抬起头,眼中瞬间燃起一丝微弱的火苗,像溺水者看到浮木。
“真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真的!”刘三咧开嘴,露出焦黄的牙齿,笑得狰狞,“可你有吗?”
那簇微弱的火苗,噗地一声,被这残酷的现实吹灭了。她所有的钱,连同那张车票,都遗失在了命运的狂风里。眼泪毫无征兆地汹涌而出,不是因为自己的绝望,而是因为那五块钱——那五块本该变成母亲嘴里一块亮晶晶、甜丝丝的冰糖的钱!那甜味,成了此刻喉咙里最苦的毒药。
日子像村口那条浑浊的小溪,缓慢、凝滞,裹挟着绝望的泥沙流淌。逃跑的念头从未熄灭。一次,趁刘三上山,她赤着脚,像受惊的鹿,沿着陡峭的羊肠小道狂奔。荆棘划破脚踝,山石硌得脚底渗血。眼看山口在望,却被两个扛着锄头的村民堵了回来。
“买来的媳妇还想跑?刘老汉的钱是大风刮来的?”粗鄙的咒骂和推搡像冰雹砸在身上。她被推倒在泥泞里,冰冷的泥浆糊了一脸一身。
刘三闻讯赶来,手里拎着一根手腕粗的棍子,脸色铁青。他没打她,只是用那双被酒精泡得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那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剜得她骨头缝里都冒着寒气。当晚,她的鞋不见了。她光着脚踩在冰冷的土炕上,脚底的伤口沾满了灰尘和草屑,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死吧。这个念头疯狂滋长。
第一次,她摸到了灶台上的镰刀。冰冷的铁器贴着腕部的皮肤,那里能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搏动。母亲的声音却在耳边响起,遥远却清晰:“敏儿,活着,活着就有盼头……”她的手抖得握不住镰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第二次,她找到了藏在灶膛角落的老鼠药。那刺鼻的苦味让她胃里翻江倒海。她闭着眼,抓了一大把塞进嘴里。苦涩瞬间弥漫了整个口腔,麻痹了舌头。还没等咽下,却被进来拿柴火的刘老汉撞见。半瓢刺鼻的肥皂水被强行灌下,抠着喉咙催吐,吐得胆汁都出来了,天旋地转。
第三次,她扑进了村后冰冷的河水里。刺骨的寒意像千万根钢针扎进骨髓,瞬间夺走了呼吸。水呛进肺里,火烧火燎地疼。就在意识即将涣散时,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她的头发,粗暴地将她拖上了岸。她躺在冰冷的鹅卵石上,望着灰蒙蒙、永远也望不透的天空,只有冰冷的河水从发梢滴落,砸在石头上,也砸在她死寂的心上。为什么连死,都这么难?
1996年的秋风吹黄了山里的树叶,也吹来了一丝意想不到的“仁慈”。刘三突然说带她回台江县红苕沟探亲。艳敏的心像被丢进油锅,瞬间沸腾又瞬间冷却。她连夜缝了个小小的布袋,把偷偷攒下的二十多个鸡蛋拿到邻村换了钱,仔细地缝进裤腰的夹层里。那点钱,是她卑微的希望,是通向自由的最后一张船票。只要见到爹娘,他们一定会救她!
推开那扇熟悉的、吱呀作响的院门,母亲正佝偻着背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看见她的瞬间,母亲手里的针线“啪嗒”掉在地上,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震惊,继而涌起滔天的悲恸。“崽啊……”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母亲扑过来抓住她的手,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颤抖得厉害,滚烫的眼泪大颗大颗砸在艳敏的手背上,灼痛了她的皮肤。
晚饭时,父亲蹲在灶膛前,沉默地吧嗒着旱烟,劣质烟草的辛辣味弥漫在低矮的土屋里,呛得人想流泪。昏黄的灯光下,父亲脸上的沟壑更深了,背也更驼了。艳敏扑通跪倒在爹娘面前,积压了两年的委屈、恐惧、绝望像决堤的洪水,她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被拐卖、被囚禁、被毒打的非人遭遇。
母亲把她拉进昏暗的里屋,油灯的光晕在母亲憔悴的脸上跳动。“崽啊……”母亲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无尽的悲凉和无奈,“人家……人家花了两千七……那是多大一笔钱啊!再说……你这身子……结过婚的闺女……回来,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谁还要啊……”
每一个字都像淬毒的冰锥,狠狠扎进艳敏的心脏。她看着母亲鬓角刺眼的白霜,看着父亲被生活压垮的脊梁,那点微弱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了。原来,家,也回不去了。她不再是爹娘捧在手心的闺女,而是被两千七百块买断的、一件有了瑕疵的货物。她默默地解开裤腰,掏出那个缝得紧紧的小布袋,里面是几张被汗水浸得发软的毛票。她塞进母亲冰凉的手里:“娘……抓药……”
母亲的手哆嗦着,攥紧了那几张皱巴巴的钱,泪水无声地滴落,迅速在纸币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像永不愈合的伤疤。
回下岸村的路上,破旧的长途汽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窗外,连绵的群山像无数沉默而狰狞的巨兽,张牙舞爪地向后掠去。艳敏靠着冰冷的车窗,眼泪早已流干,只剩下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和冰冷。她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那张年轻的脸上刻满了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沧桑和死寂。她知道,就在这个秋天,那个名叫艳敏、对家和未来充满憧憬的姑娘,彻底死了。活下来的,只是下岸村刘三的“屋里人”。
2000年的春天,下岸村贫瘠的山坡上,野山桃开得没心没肺,粉白的花朵在料峭的风里颤巍巍地绽放,给灰黄的山坳涂抹上一点脆弱的生机。村支书佝偻着背敲开刘家吱呀作响的院门时,艳敏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给三岁的儿子喂奶。怀里的女儿裹在旧棉布做的襁褓里,小脸冻得通红,像两个熟透的小苹果。
“艳敏啊,”支书蹲在门槛上,吧嗒着旱烟锅,烟雾缭绕着他愁苦的脸,“村小的王老师……熬不住,走了。娃们……快散了架了。你……你读过书,识得字,能不能……能不能去顶几天?好歹……别让娃们当睁眼瞎。”
艳敏的手顿住了,奶水濡湿了儿子的衣襟。她低着头,看着儿子吮吸时满足的小脸,声音低得像耳语:“俺……俺不行。早忘光了。”她害怕。害怕站在人前,害怕那些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害怕那片小小的讲台会照见她灵魂深处无法愈合的伤疤。
“咋不行?”支书把烟锅在鞋底上重重磕了磕,烟灰簌簌落下,“你看狗剩,丫蛋,都七八岁了,自己的名字画得像鬼画符!再没人教,就跟咱们似的,一辈子困死在这山窝窝里,连个信都写不明白!”
“一辈子困死在这山窝窝里……”这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针,猛地刺进艳敏早已麻木的心脏。她想起了初中毕业时,班主任拍着她的肩膀叹息:“艳敏,你是块读书的料,可惜了……”可惜了。这三个字,像命运的判词,如今在这太行山的深处,又冷冷地回响起来。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艳敏把睡眼惺忪的儿子交给婆婆,怀里抱着女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村东头那间孤零零的土坯房——村小。推开吱呀作响、快要散架的木门,一股潮湿的霉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窗户用破塑料布勉强糊着,被风撕开的口子呼呼往里灌着冷风。所谓的黑板,是一块刷了墨汁的破木板,早已斑驳龟裂。十几个孩子挤在几条破旧的长条板凳上,小脸脏兮兮的,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但那一双双望向她的眼睛,却像山涧里未被污染的溪水,清澈,懵懂,带着一丝怯生生的期待。
“老……老师好!”一个扎着稀疏羊角辫的小姑娘,丫蛋,怯生生地站起来,小声喊道。
这一声“老师”,像一道微弱的电流,瞬间击中了艳敏。她捏着半截粉笔的手指猛地一抖,“啪嗒”,粉笔头掉在地上,摔成两截。她慌忙弯腰去捡,粗糙的土墙仿佛要将她吸进去。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站直,颤抖着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人”。粉笔划过粗糙的木板,发出艰涩的“吱嘎”声,留下一个歪歪扭扭却无比庄重的印记。
没有课本,她凭着记忆,把那些沉睡在心底的拼音、汉字、算术一点点唤醒,写在黑板上。粉笔灰簌簌落下,沾满了她的手指、袖口,像一层薄薄的雪。没有教具,她用河滩捡来的小石子教孩子们数数,用树枝在泥地上划出“a、o、e”。她教孩子们念“天、地、人”,声音起初干涩发颤,渐渐变得清晰有力。她教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升……”童稚的歌声从破败的土坯房里飘出去,惊飞了屋檐下做窝的麻雀,也惊醒了这个死寂的山村。
有一天,教到“家”字。她在黑板上用力写下这个字,问:“娃们,你们的家在哪?”
“下岸村!”“刘家沟!”“后山洼!”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喊。
只有丫蛋,低着头,声音细若蚊呐:“老师……俺想让俺娘回家……”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艳敏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她几乎窒息。她别过脸去,手指用力抹过黑板边缘的灰尘,指尖传来粗粝的痛感,才勉强压住眼眶里汹涌的酸涩。她想起自己远在台江县红苕沟再也回不去的家,想起娘塞给她的红薯面饼,想起那张被风吹走的车票。放学后,她把丫蛋拉到怀里,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颗用糖纸包着的水果糖——那是去年一个过路货郎看她可怜给的,她一直没舍得吃。糖纸已经磨得发毛了。“丫蛋,”她把糖轻轻放进女孩冰凉的小手里,“好好念书。念好了书,认得了路,长大了……就能自己找家。”
教书,成了艳敏灰暗生命里唯一的光源。这光,也在悄然改变着周遭的一切。刘三醉酒打她的次数明显少了。有时她批改作业到深夜,他会默默地在灶膛里添把柴火,让屋里暖和一些。一次,她发现教室的窗户破洞被人用木板仔细地钉上了,虽然歪歪扭扭,却挡住了刺骨的寒风。她问是谁做的,刘三闷头劈着柴,瓮声瓮气地说:“风大,吵着娃们念书。”
村民们见了她,不再喊“刘三家的”或者“买来的”,而是带着几分生疏的恭敬喊一声“艳老师”。初冬的一个清晨,她推开教室门,发现讲台上放着几个还带着泥土的萝卜和一小袋金灿灿的小米。没人说话,但那份沉甸甸的暖意,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她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孩子们在简陋的土坪上追逐笑闹,山风吹起她枯黄的发丝,也吹动了心底那潭沉寂已久的死水。她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这片曾囚禁她、差点吞噬她的山坳,这片贫瘠的土地,用另一种方式,接纳了她。而她,似乎也在这间破败的土坯房里,在孩子们清亮的读书声中,找到了扎根的缝隙。那些稚嫩的声音,像一颗颗渺小却倔强的种子,落在她龟裂的心田上,也落在孩子们懵懂的心智里,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日子在粉笔灰的飘落和孩子们朗朗的书声中流淌。刘三的变化是缓慢而坚实的。他不再酗酒,脸上的横肉渐渐被风霜刻画出些许温和的线条。他开始笨拙地学着劈更细的柴火,好让艳敏批改作业时手不那么冷。他甚至会偷偷观察她握粉笔的姿势,有一次,在油灯下,他拿着半截烧黑的木炭,在废弃的烟盒纸上,歪歪扭扭地画着“人”字,像一个最笨拙的学生。
2005年的秋天,山桃树的叶子开始变黄。一个偶然路过的陌生人(后来知道是曲阳县的农民摄影家向阳)被教室里传出的读书声吸引。他站在窗外看了很久,拍了几张照片。艳敏发现他时,他有些局促地解释,说这景象很美。艳敏只是点点头,继续教孩子们念课文。她不知道那些照片后来去了哪里,也不关心。她的世界,就在这间土坯房里,在这些仰望着她的孩子们身上。
外界的喧嚣终究还是来了。记者们扛着机器来了又走,问着千篇一律的问题。艳敏的回答总是很简单:“俺就想让娃们多认几个字。”荣誉的光环(“感动河北”)曾短暂地笼罩过她,红呢子褂穿在身上像一层陌生的壳。聚光灯下的掌声遥远而虚幻,远不如丫蛋学会写自己名字时那羞涩又骄傲的笑容来得真实温暖。
光环之下,阴影也随之而来。那些窃窃私语像山间的毒藤蔓,悄然滋生。她走在村里,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有次在河边洗衣服,清晰地听到石头后面几个妇女的议论:
“装啥好人?还不是靠那点破事出的名!”
“就是!闹得外面都知道咱村买媳妇,丢人现眼!”
“听说上面拨钱修教室,谁知道进了谁的口袋……”
艳敏握着棒槌的手猛地收紧,指节发白,手背上的青筋根根凸起。一股积压了十几年的怒火混合着无法言说的委屈,像岩浆般冲上头顶。她猛地站起身,河水打湿了她的裤脚也浑然不觉,朝着声音的方向大声喊道:
“俺被拐来锁在屋里的时候,你们谁给俺递过一碗水?俺被刘三打得半死的时候,你们谁拦过一句?俺在这破屋里教你们娃认字的时候,你们谁说过一句好?!现在倒来嚼舌根!俺艳敏行得正坐得直!这书,俺教定了!”声音在山谷间回荡,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玉石俱焚般的决绝和力量。那几个妇女讪讪地闭了嘴,缩着脖子溜走了。
刘三不知何时站在了她身后不远处的杨树下,默默地递过来一块干净的粗布毛巾。这些年,他学会了沉默的守护。艳敏接过毛巾,胡乱擦了擦脸,没看他,也没说话,蹲下身继续用力捶打着衣服,水花四溅。有些隔阂,像山里的石头,硬而冷,但共同经历的风雨,也能在石缝里长出些沉默的苔藓。
2014年,山桃花又开了,粉白如云。一位风尘仆仆的律师找到她,带着一丝希望和更多的歉意。他告诉她,当年拐卖她的人贩子,线索断了又续,续了又断,最终因为证据和时间(二十年追诉期)的问题……希望渺茫了。
那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把群山染成温暖的橘红色。艳敏独自坐在教室门口冰凉的石阶上。晚风带着山桃花清冽的香气拂过她的面颊,也拂动了她鬓角早生的白发。她摊开手掌,常年握粉笔的手指关节粗大,指腹和掌心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像一块粗糙的磨刀石。二十年了。她想起十八岁的那个夏天,车站喧嚣的人潮,那张被风卷走的绿色车票,那个对未来还懵懂着、憧憬着的自己。
她抬起头,望向教室。新装的节能灯散发出明亮柔和的光,透过塑料布窗户,照亮了里面一排排简陋但干净的桌椅,照亮了墙上贴着的孩子们的画和奖状——那是他们用知识和希望一点点装点的“星空”。灯光穿透了山村的浓重夜色,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温暖、坚定。
她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脸上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历经劫波后的平静和一种近乎虔诚的笃定。她推开门,走进那片明亮的灯光里。粉笔盒静静躺在讲台上。她拿起一支粉笔,掂了掂分量,然后转身,在黑板上用力地写下一行字,字迹沉稳有力:
“明天默写:《我的家乡》。”
窗外,山桃灼灼,在暮色中安静地燃烧。山风依旧在吹,吹过沉默的群山,吹过简陋的校舍,吹过孩子们梦想的嫩芽,也吹过艳敏染霜的鬓角。这风声,不再是囚笼的哀鸣,而像一首深沉而悠长的歌,吟唱着生命的韧性与救赎——它讲述着一个被折断翅膀的灵魂,如何在最贫瘠的土壤里,用另一种方式重新飞翔的故事。她的人生,或许永远无法逃离这口“锅底的山坳”,但她亲手点亮的那盏灯,却照亮了一条让孩子们走出去、让希望走进来的路。这,就是她与命运抗争的勋章,是她用血泪浇灌出的,最动人的人间真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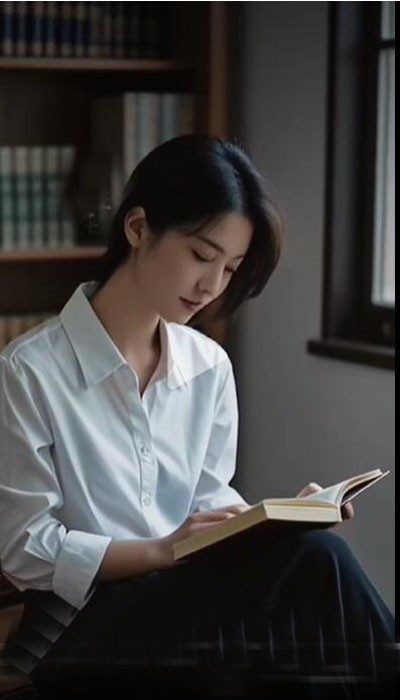



欢迎访问北京智慧子月科技有限公司
热点内容
Hot content
视频推荐
VIDEOS